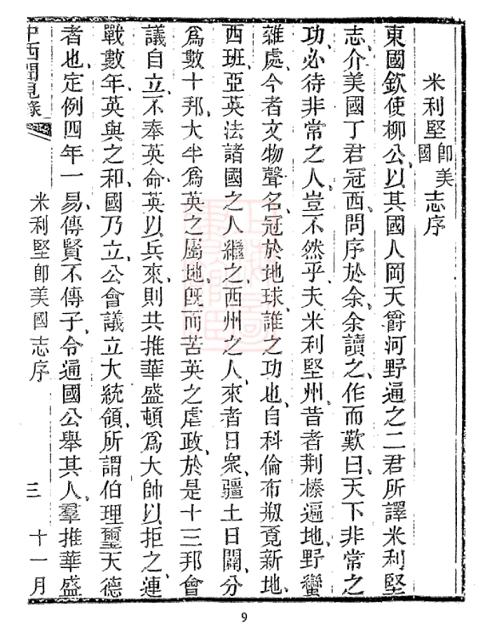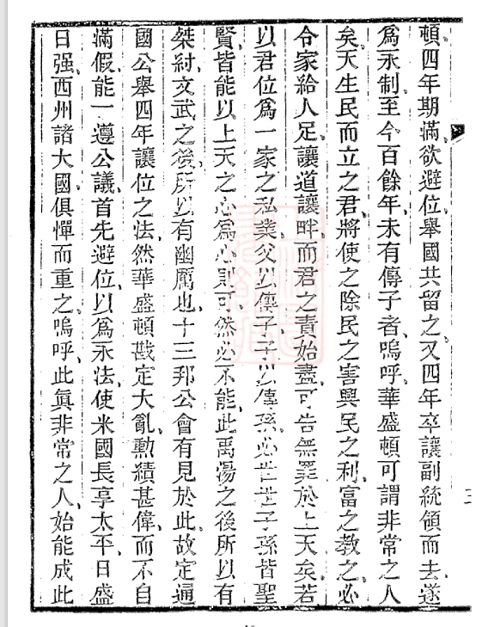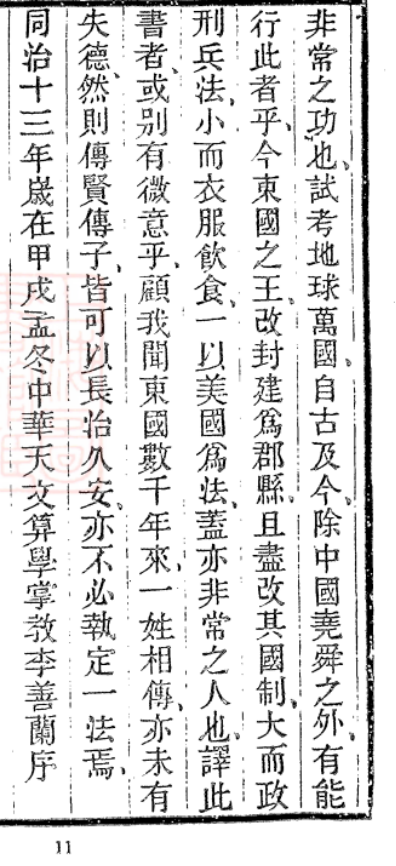当前位置 : 洛城漫话
 发布日期:2024/9/21
发布日期:2024/9/21
 来源:
来源:
 打印
打印
蔡德貴
胡適的學生蘇雪林在《天問裡的後羿射日神話》(《東方雜誌》1944年第40卷第8號)裡就開始研究中外早期的文化交流,後來發現《山海經》裡有希伯來文的音譯詞彙,從而斷言早在幾千年前中外之間的交流就有過幾次高潮。1953年美國女學者亨麗埃特·墨茨博士(Henriette Mertz,1898年-1985年)對《山海經》詳細考證,然後按圖索驥,邊走邊考察,在撰寫出的《淡淡的墨痕》(中譯本崔岩峙等譯:《幾近褪色的記錄——關於中國人到達美洲探險的兩份古代文獻》,海洋出版社1993年)裡說:“過去2000多年一向被中國人認為是神話的《山海經》,不是神話,而是真實的文字記錄。珍藏在中國書庫中的這部文獻提供了充分的證據表明,早在西元前2000多年中國人便已到達美洲探險。”她認為第一份文獻《山海經》證明在西元前23世紀中國人已經到達美洲探險了,而第二份文獻《梁書》則通過南朝和尚慧深雲遊東夷扶桑國的記載,證明中國人第二次到美洲是西元5世紀。近年由於三星堆的發現,證明這種觀點有道理,此言不虛。只是那時候還沒有美國。
美國獨立的時間是1776年7月4日,這一年是清朝乾隆四十一年。在資訊不發達的時代,大清國4億中國人的絕大多數,尚不知道那個建國之時不足300萬人口的彼岸之國,以至於開始介紹美國的時候,譯名眾多。
1795年,英國商人在廣州進行貿易,他們稱呼美國為“呵嘪哩噶”。這是最早的美國譯名。19世紀初期,清朝官方以“咪唎堅”稱呼美國。
而中國非官方人士最早介紹美國的,是1820年由航海家廣東嘉應人(今梅州縣)謝清高口授,其同鄉楊炳南記錄的《海錄》(即《海外番夷錄》),此時距離美國1776年獨立大概半個多世紀,但《海錄》僅簡略地提到“咩裡幹”(美利堅)國的一般情況,而且並不準確,說“咩裡幹國,海中孤島也,疆域稍狹”,所以有人批評這種說法,估計可能本人沒到過美國。楊炳南《海錄序》則解釋說:“向來志外國者,得之傳聞,證于謝君所見,或合或不合。蓋海外荒遠,無可征驗;而腹佐以文人藻績,宜其華而匙實矣。謝君言甚樸拙,屬餘錄之,以為平生閱歷得藉以傳,死且不朽。”把美國叫“咩裡幹國”,被當時許多人所接受。那時人們一般稱美國為“咩裡幹”外,還有“咪唎堅”、“彌利堅”、“米利幹”、“米利堅”、“花旗”、“亞墨裡駕花旗”等,其中以“咩裡幹”最為流行。清朝史籍其他對美國的譯稱還有:梅立根、米里堅、育奈士迭、美立根、美利駕、美利加、兼攝邦、合眾國、墨國、北亞墨利加、亞國、米、米國、花旗国等。
1838年,第一個來華的美國傳教士稗治文還提到更多的譯名:
夫美理哥合省之名,乃正名也。或稱米利堅、亞墨理駕、花旗者。蓋米利堅與亞墨理駕二名,實土音欲稱船主亞美理哥之名而訛者也。至花旗之名,則因國旗之上,每省有一花,故大清稱為花旗也。至所雲美理哥者,即亞美理哥也。合省者,因前各治其地,國不相連,政無專理,後則合其省而以一人為首領,故名之曰合省。是則今之稱美理哥者,固正而不訛。後雲合省者,亦正而不訛也。(高理文(即稗治文):《美理哥合省國志略》第2卷,道光十八年,新加坡堅夏書院1938年藏版,第4頁。另外有《亞美理駕合眾國志略》,道光二十六年)
1844年《望廈條約》裡是“大亞美理駕合眾國”,1901年《辛丑合約》裡是亞美理駕合眾國,1913年,中華民國與美國建交,將美國的譯名定為“美利堅合眾國”,簡稱“美國”,並沿用至今。
1840年前後,中國文化思想界開始出現研究西方的新動向,1839年林則徐的《四洲志》(美國的譯名是育奈士迭國)、1842年魏源的《海國圖志》(彌利堅,後夏燮的《中西紀事》沿用)、1848年徐繼佘的《瀛環志略》(米利堅合眾國),都比較系統地介紹了美國的地理沿革、政治歷史、物產民情。他們所用的材料,不外是當時翻譯的西方作品。
晚清外交家浙江德清人傅雲龍的《美利加合眾國圖經》列出在《東西洋考·每月統紀傳》(1833)《美理哥合省國志》(1838年)等等著作中,除美利加外,還記錄有美利駕、美利堅、米利堅、彌利堅、墨利加、默里駕、美理哥、美理格、美利剛、彌利哥以及花旗、育奈土迭、咩裡幹、合眾國、尤乃特司台茲、尤乃司台茲、米利駕聯邦等等。而華夏中心論者的譯名則稱美國為“米夷”或“米酋”,他們瞧不起這個蠻夷之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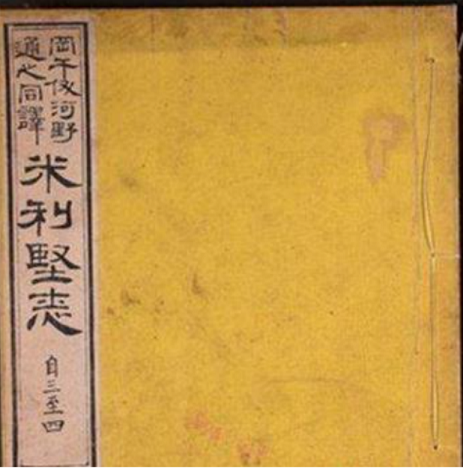
惜哉。
1855年,中國人開始詳細介紹美國之父華盛頓將軍,據《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1853-1856.FULLTEXT)第四號(V.Ⅲ,NUM.4.APRIL.1855)《雜說編》:
華盛頓者,亞麥裡迦人也。才兼文武,為國效忠,其所謂公爾忘私,國爾忘家者也。自少年時,義氣奮揚,動皆中禮,言辭真實,屏絕浮誇。亞麥裡迦合眾國,莫不仰慕其為人,至今猶樂道之。余今節取其少年一事,列於貫珍。俾中國童子讀而慕之,或可感發心志,是所厚望。華盛頓才六歲時,有友送以小斧一柄,得斧後,喜氣揚揚,隨處玩弄,遇物必斫,此童子不識不知之性,大抵皆然也。家園中植有櫻樹一株,種異凡品,其父愛惜,有若異珍。一日華盛頓攜斧入園,將纓樹戕賊迨盡,次日其父遊園,看見櫻樹支分節解,遂大發雷霆,聚集家人詢問曰:園中櫻樹,吾愛所鐘,雖人以多金來購,吾亦不舍,今被惡人戕害乃爾,吾必窮究此人,以消吾恨,家人皆推不知,喧嘈間,華盛頓自外入堂,手攜小斧,父問曰:吾兒可見伐櫻樹之人乎?華盛頓見父怒容滿面,家人觳觫情形,寸心惶恐,初不敢言,頃之,乃曰:誑言我不敢說,此,父親大人所知,園中櫻樹實我用此斧戕害也。其父聞子此言,變怒為喜,滿面歡容,欣然曰:嗣後乃知吾子不說誑言,是吾家大幸,雖櫻樹花可成白金,實可成黃金。吾複可惜哉?
到同治十三年(1874年),美國人丁韙良、英國人艾約瑟等創辦於北京的《中西聞見錄》,首先發表了浙江海甯人、京師同文館首任算學總教習李善蘭,應京師同文館同事丁韙良之邀為日本人岡天爵、河野通之二君所翻譯的《米利堅志》寫的序。李善蘭開始使用“美國”的稱謂,注明米利堅,即美國。同年美國林樂知主編《萬國公報》開設了“大美國事”的專欄,1875年《萬國公報》重發了李善蘭序。從此美國開始為廣大中國人所接受。李善蘭可以說是清朝第一個“親美派”的數學家、天文學家,被譽為改變近代中國的科學家,有很高的學術地位。
他為什麼稱“美國”?是因為他認為,美國這個地方,“昔荊榛遍地,野蠻雜處,今者文物聲名,冠於地球”, “自科倫布創覓新地,西班亞英法諸國之人繼之,西州之人來者日眾,疆土日辟,分為數十邦,大半為英之屬地。既而苦英之虐政,於是十三邦會議自立,不奉英命。英以兵來,則共推華盛頓為大帥以拒之,連戰數年,英與之和,國乃立,公會議立大統領,所謂伯理璽天德者也。定例四年一易,傳賢不傳子,令通國公舉其人,群推華盛頓。四年期滿,欲避位,舉國共留之,又四年,卒讓副統領而去,遂為永制,至今百餘年未有傳子者。嗚呼,華盛頓可謂非常之人矣!華盛頓勘定大亂,勳績甚偉,而不自滿假能,一遵公議,首先避位,以為永法,使米國長享太平,日盛日強,西州諸大國俱憚而重之。嗚呼,此真非常之人,始能成此非常之功也。”(《中西聞見錄》1874年11月第.28號《米利堅〔即美國〕志序》)這是李善蘭所稱的美國之“美”的原因。
清政府駐美大使崔國因(1892年離任)在《出使美日秘日記》裡已經使用“美國”的譯名,但1893年彭光譽代表清政府參加美國芝加哥世界宗教議會,提供了《說教》的長篇論文,後來因為光緒有批閱,以《御覽說教》正式出版,該論文裡使用了美洲合眾國(原注:一、尢恩藹梯依諦,二、司梯愛梯依司,三、愛姆依阿藹西愛)的譯名,說明那時候譯名還沒有統一。
一般學者,甚至通俗讀物裡,還有人繼續沿用“米利堅”。1902年,任湖南經心、江漢兩個書院的輿地學教習姚炳奎出版了《經心書院輿地學課程》,使用非常之廣,影響非常之大,徐繼畬因之,仍然延續“米利堅”之稱。可以說,從“咩裡幹國”到“米利堅”,再到“美利堅”,美國的譯名更為適合中國人的語言習慣,更為上口。就像當初的“蝌蚪啃蠟”如果不是“中國文化的國際使者”蔣彝教授改譯為“可口可樂”,那這個美國飲料可能還不能像現在這樣被中國人廣為接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