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 : 历史档案
 发布日期:2023/4/15
发布日期:2023/4/15
 来源:國際日報
来源:國際日報
 打印
打印
(接上期)
聽到華國鋒講要繼承毛主席遺志,繼續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我們暗暗地想,這樣的政策還能持續多久。在我接觸到的那些老幹部、老教授和普通的市民中,似乎誰都認為,毛主席死後,鄧小平再次複出的希望並不渺茫。
19日,我們五人在天安門廣場合影,背景裏有偉大領袖毛主席永垂不朽的橫幅標語。28日,因國慶到來,北京遵循往年慣例,要趕外地來人回原地,五人也就此分手。袁、方倆人回上海,宋一平則由李副部長的夫人陪著上哈爾濱省郵電總局落實到我縣漠河郵電所工作的事。只有賀南南還沒下決心開後門調走,便和我一起回黑龍江生產隊。
回去的路上,火車經過了被大地震摧毀成一片廢墟的唐山,那種慘景讓人看了終生難忘。
火車進入大興安嶺後,這裏已經下過雪了。有位外國詩人說過,“冬天已經來了,春天還會遠嗎。”通過這次奔喪,我感到了民心所向,看到了國家的前途希望的曙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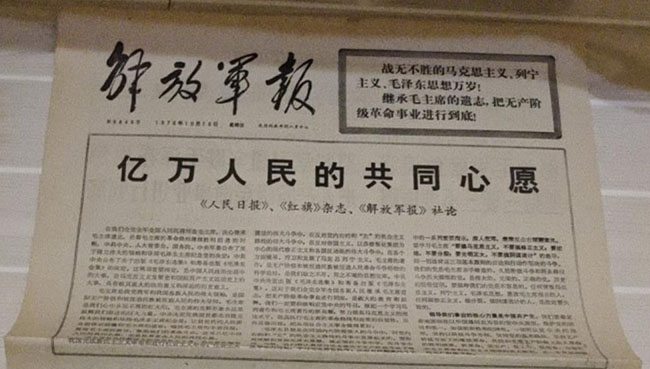
10月15日以後,除了美英日蘇的電臺廣播了江青等四人幫被抓的消息外,北京的朋友們的報喜信件和各種內幕報導也紛至遝來。他們告訴我們,你們的插隊生活就要結束了,中央馬上就會著手解決全國的知青問題。
10月22日,北京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集會遊行,歡慶粉碎四人幫的勝利。又過了幾天,中央人民廣播電臺播放了貝多芬的第五命運交響曲。作為一個普通的知青,我親身感受到了這場歷史巨變的發生,我和人民一起經歷了喜怒哀樂,我相信人民的力量是偉大的,這就是國家的命運,任何想阻擋歷史潮流前進的人必將被釘在恥辱柱上。
我再看到江青在電視上公開露面時,她已經是作為犯人受審了。
六面對死神(上)
受當時政治宣傳的影響,來黑龍江邊境農村插隊的知識青年有不少是自願報名的,他們渴望在邊境的艱苦鍛煉和血汗洗禮中,讓自己也成為和父輩那樣的英雄人物。哪里的活最艱苦,哪里的任務最危險,他們就自告奮勇地沖在前面,他們的許多人逐漸取代了當地老鄉,成為生產勞動和保衛邊疆的最有生氣的主力軍。當地的領導也樂意把最艱苦的任務譬如修路,蓋橋,建水庫等等交給知青去完成,而死神就在此時向知青們悄悄地走來。
知青們不僅在黑龍江省留下了豐碩的勞動果實,有時在那裏也會留下鮮血甚至生命。
就拿1970年在呼中的原始森林裏修那條戰備公路來講,就有三四個十七八歲的知青被炸山飛來的石頭打得腦袋開花,被砍倒的大樹壓得血肉模糊,長眠在林中。當時大家只想趕進度,比速度,也不重視安全保護,加之一切合理的規章制度都被打破,上級只是給各個生產隊派任務,就是崩山炸石頭這種人命關天的活也是聽任各隊自行其事,整個工地現場缺乏統籌管理,險象橫生。
點火之後,大家就數炮的響聲來判定是否有啞炮,如果這時其他生產隊人員也在崩山的話,爆炸聲此起彼伏,就有可能數錯。你認為自己隊的炮全響過了,其實還有沒響過的炮,等你一走進工作現場,最後一炮剛好炸響,大小石頭如雨點般似地撲天蓋地飛來,你又忘記戴好安全帽,那就慘了,輕者傷筋斷骨,重者一命嗚呼。
有時其他生產隊崩山的石頭也會飛到我們躲避的安全地帶,這可謂是飛來橫禍。我隊有位知青,從小彈的一手好鋼琴,文革前在市里的少年鋼琴比賽中還得過名次,剛去修路工地第三天,就被一顆飛來的小石子打斷了左手的小指和無名指,1973年落實知青政策時雖說是以此傷較早地病退回到上海,但再也無法重續他成名成家的舊夢。
現在的年輕人來到國外,雖然也有各種非正常傷亡,車禍,疾病,自殺等等,但那時有些知青的非正常傷亡有時更帶有一種英雄主義和悲劇的成分。
還在1969年的時候,上海的報紙上就宣傳過一個在黑龍江插隊的叫金訓華的上海知青,他原是上海中學紅衛兵代表大會的委員,本來可以留在上海工礦,自己卻主動報名去邊疆,號稱“一生交給黨安排”,結果在黑龍江倒開江發大水的時候,為了撈回隊裏幾根漂走的圓木,跳下水去而被白白淹死。這種現在看來毫無價值的犧牲,當時卻被當局大肆渲染成為一種英雄行為,要大家學習。
那個時代在黑龍江鍛煉過的許多知青,在潛意識中或許確實存在著一種理想主義和英雄主義,先人後己,不怕苦,不怕死,一旦有需要,犧牲生命也在所不惜。

我們公社有一個知青,有年冬天和大家坐卡車去林區伐木,卡車翻到路邊,把他摔昏了,他醒來的第一句話便是“同志們怎麼樣了”,和報紙電影中英雄的口氣如出一輒,周圍的人調侃他,“怎麼樣了?還是喝苞米碴子粥”,把他弄得好尷尬。其實他不一定是裝的,現在的人很難理解這點。
我隊有位知青回滬頂替父親,在遠洋輪上當了海員,八十年代有次在海上,機艙裏兩次發生火事,他勇敢地沖入火中,關掉了閥門,雖說受了燒傷,卻為撲滅火事立了大功。誰知回來後,有位局領導在找他談話時,不懷好意地問他,人都是自私的,為什麼別人不敢沖上去,只有你不怕死,你有沒有什麼個人動機。因為一時找不到火事的發生原因,他竟被懷疑了好長時間,直到三個月後部裏的調查組下來排除了他縱火的可能性,搞清了事故真相,他才被恢復了原來的二管輪的職務,得到通報表揚。
在我八年的插隊生活中,兩個熟悉的朋友在死神的微笑面前那種從容不迫的神態在我心中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
1971年底,我去金山大隊玩,那裏有不少從幼稚園,小學,中學就已經熟悉的朋友們,其中就有許元,在家是老五,父母和大家都管他叫小五子,時間長了大名倒沒人叫了。
小五子的父親原是山西五臺山一帶的小石匠,十五歲時和二哥一齊給地主幹活時,一隊紅軍路過他們村,宣傳員們說,日本鬼子佔領了東北,窮苦的弟兄們,趕快參加紅軍吧,紅軍是要打日本鬼子的,是幫窮人打天下的隊伍,趕走日本鬼子,打下天下,你們大家就有田耕,有飯吃,還可以到城裏去做官。二哥一聽,想想與其天天給人幹活還吃不飽飯,不如去當兵闖一闖,反正家裏有大哥孝敬老娘。於是便扔下手裏的工具,帶著弟弟隨著村裏的幾個青年加入了紅軍,後來又變成了八路軍。
小五子爸爸參軍時年紀小,個子也不高,在部隊裏當了個小號兵,還沒打幾仗,二哥便被打死了,他大腿上也吃了顆日本子彈,還生了一身癩皮瘡,送進部隊醫院。院長看他長得聰明伶俐,便把他留下當了勤務員,於是小五子爸爸便一直在部隊醫院工作,和院裏的女護士結了婚。後來轉到華東野戰軍,是華野第一支坦克部隊醫院的創始人之一。
1949年進了上海後,在衛生局當了副局長,有一年回山西老家給老娘掃墓時,才知道村裏出來跟著共產黨打天下的二十來個人,只有他是唯一的倖存者,還當上了官,其餘人都在抗日戰爭和解放戰爭中戰死了。不禁感慨萬分,老拿這事教育我們這些小孩不要忘本,還把四個兒子都送去當了兵。
1969年中蘇邊境武裝衝突爆發,小五子中學畢業面臨上山下鄉,小五子媽想讓小五子留在上海,還在五七幹校等待“解放”的他爸卻說:“怕什麼,小五子就是和蘇聯人打仗打死,咱們還有四個兒子呢。”於是他找到學校革委會的領導,要求讓小五子去邊疆最前線去插隊。我們開玩笑說,小五子是被他父親分配到呼瑪來的。
他大哥在哈軍工畢業後去了海軍工作,71年秋天寄來一首水調歌頭詞,“清光一萬裏,雲港蔽星舟。閱盡秋色,燈火圈圓唯神州。列寧故土淪陷,紅河子孫離散,問君知幾秋?倍思手足親,何己醉溫柔?濤聲息,風行疾,披瑩霜,躍步飛升,欲攀天纜操天舟,登峰槍挑紙虎,下海纓縛叛蝤,佳節共環球。有血便無淚,斷頭不低頭”。
小五子也回了幾首詩,我還記得其中好幾句,“遠瞻蘆蕩軍,白髮欺黃忠,更兼兄弟輩,縱橫皆英雄。依呀黃口兒,猶唱紅燈頌。隨征已三載,帳前無寸功。未繼登山止,得展壁輝宏。吾亦將門子,何獨怯青峰。千文能奮筆,點謀不存胸。白食千家米,赭顏顧江東,思絕沖冠起,提酒掩倥惚”。
但是中蘇邊境儘管緊張,在我們知青去後,並沒有發生過大規模的武裝衝突,小五子那種“炮火起處獻忠魂”的豪言壯語只能變成“改觀改魂清己垢”的實際行動,在生產勞動中表現得十分積極,幹活從不肯落在別人後面。
有次當地的老鄉對我們一部份知青和他們拿一樣多的工分不滿,提出要比賽割黃豆,看誰割得快。個子矮小的小五子作為男女知青的代表之一,和老鄉中活幹得最好,工分拿得最高的兩個男青年比。割黃豆其實沒有多大技巧,就是看誰有耐力,少直腰就能割得快。
開始一小時他和老鄉不相上下,一直沖在割豆隊伍的最前面,因為一條壟有五六裏地長,老鄉也忍受不了彎腰的苦,不時直腰喘口氣,小五子不小心把手指割了個口子,鮮血直流,他毫不吭聲,和幾名男女知青幾乎是一口氣割到頭,又回來接應大家。
老鄉們不服氣,檢查品質時,才發現小五子割的那條壟上的血有一裏多長,從此對知青幹活口服心服。
12月26日,是毛澤東的生日,晚上我和大家吃了麵條,又在小五子他們宿舍裏聊天。因為來插隊的知青人數要比當地老鄉還要多,所以蓋了幾排象兵營那樣的長房子,一排房子裏又有好幾個大房間,門是分別開的。小五子住的那間屋裏有三十來個人,分上下鋪睡,隔壁便是民兵連連部。晚上九點多鐘,小五子打著赤膊,只穿一條短褲,站在屋子中間的用空汽油桶做的大鐵爐前擦身,一面吹口哨,吹口哨是他的絕招,他能把芭蕾舞紅色娘子軍的全曲從頭到尾吹出來。忽然隔壁連部裏“砰”的一聲槍響,這邊小五子也撲通一聲倒了下去,我們還在發愣,只見小五子用手捂著肚子,鮮血從他手指縫裏不停地淌出。
“我中彈了,快拿個碗給我”,他輕聲地喊著。有人趕快遞上了一個搪瓷碗,小五子著急地搖了搖頭,“不行,這容易感染,我的腸子流出來了,要瓷碗”。大家趕緊手忙腳亂地把他扶上鋪。這時屋門也被人拉開了,有個當地青年探進頭來看了看,然後又縮了回去,驚慌地喊叫:“李金鎖,你槍走火把青年給打死了。”
屋子裏的知青馬上反應過來,好多人沖出屋去抓那個肇事者。我守在小五子身邊,幫著他用碗堵住肚子上的傷口,屋外傳來了幾十個知青的咆哮聲:“李金鎖,你跑到哪里去了,你跑得了今天,跑不了明天。”看來他們是沒有抓到那個肇事的當地民兵排長。
小五子張開眼睛,若無其事地對我笑了笑,輕聲地說:“只要血止住了,我就沒事,我爸告訴我的。你讓他們別揍金鎖,他肯定是無意的,他平時對咱們知青挺好的。”小五子的臉越來越白,不一會就失去了知覺。
隊裏的赤腳醫生來了,給他作了包紮和止血措施,打了強心針,但無濟於事,晚上十一時左右,小五子終於因流血過多而停止了呼吸,離他二十歲生日還差五天。
知青們如同受了傷的野獸,一家一戶地敲門瘋狂地找尋李金鎖,悲憤的喊叫如雷聲在村子上空滾來滾去,李金鎖的父母站在家門口,不停地向我們知青彎腰鞠躬賠禮道歉,老鄉們用驚慌的目光望著我們,誰都否認知道李金鎖的下落。
十二時,公社黨委,武裝部,派出所,醫院的人也坐北京吉普從江上趕來了。這時在生產隊領導和當地老鄉的保護下,李金鎖的父母把已經五花大綁起來的兒子交了出來。派出所的員警給跪著的李金鎖戴上手銬,並保護他免受憤怒的知青的痛打。
經武裝部的人勘察現場後,我們才知道,李金鎖擦槍忘了把剛才巡邏時上膛的子彈退出,所以一扣扳機,子彈穿過泥牆,打在宿舍梁上的木頭硬結上,又反彈到小五子肚子上,造成了小五子的死亡。
小五子的遺體放在一間空房子裏,八天後,等他媽從上海趕來後,才下葬在金山大隊附近向陽的坡上。小五子媽過去在部隊醫院給不少傷患送過葬,這次面對最疼愛的小兒子的死,表現得非常堅強,沒有哭出聲來。縣委書記問她有什麼要求,她說人死了也不能復活,現在李金鎖還被關在縣拘留所裏,請領導把他放了,也不要給他什麼處分,他們家就這麼一個勞動力。
李金鎖回隊後,接過別人轉交的小五子媽送的毛主席語錄和毛選,感動得泣不成聲,馬上到小五子的墓前連連磕頭。開始幾年,還經常去掃墓,後來知青陸續少了,他也不太去了,好像根本沒發生這回事。
1978年夏天,我回黑龍江參加大學考試時,臨行前,小五子的媽媽找到了我,她傷心地對我說:“你們這些好朋友現在都要回來了,就剩我家小五子一個人留在那裏,你考上大學離開呼瑪時,不要忘記去小五子那裏告個別,托人經常去看看他,我家小五子是喜歡熱鬧的,他最耐不得寂寞。”
我想起小五子臨死前那平靜安祥的神態,淚水不禁奪眶而出。

七面對死神(下)
誰知道,在我和生產隊其他五個知青坐海輪去大連改乘火車回呼瑪時,又經歷了一件悲劇。我們六人,五男一女,都是準備回黑龍江參加大學高考的,其中最有希望的當屬舒民安,大家都叫他阿安。他生在美國,兩歲時隨父母歸國,是文革前上海最好的重點-上海中學的六八屆高中生,還當過中學裏的團支部副書記。拿現在人的眼光來看,阿安算是連馬屁都不會拍的正人君子,疾惡如仇,一本正經到了迂腐的程度。
可就是這一特點,1975年冬天他被大家選舉當了大隊生產委員,帶著一夥老鄉和知青去幫十八站林場倒大木(伐木),這是我們那裏一年中最重要的副業。因為當時國營林場效率不高和機械化水準落後,每年冬天都要找各個生產隊的農民來幫忙完成國家計畫任務。
倒大木來錢,不光要靠大家伐的木頭立方米多,還要靠送禮打通林場上上下下的關係,譬如你把林場的頭頭給弄順氣了,他會默認你量下來的從伐木場到公路邊木材堆積地的虛假距離而不認真復查,只要你編個彎彎曲曲的運木路線,多報個幾百米距離,這樣伐下來的大木每立方米的工錢就會提高,你給林場的檢尺員送煙酒和麵粉,他每次都量大木的粗大頭,立方的數量也會無形中增加。
阿安到了林場後,打前站的許會計得意洋洋地告訴他,今年林場給我們隊定的每立方米大木的工錢要高於往年,也是各公社中最高的,雖然請林場的武主任喝了三回酒,送掉十斤豆油,一百斤白麵,還是合算。許會計要阿安繼續努力,搞好和林場檢尺員小羅的關係,小羅已經暗示要些麵粉和豆油。
阿安一聽就來火了:“我生下來就不會這一套,也不想學,現在辦什麼事,都要靠請客送禮,邪氣把正氣都給壓跑了。林場的這批人現在胃口是越來越大了,都是我們自己給喂出來的。我就是不送,他還能把我們給吃了”。
小羅開始沒吱聲,半個月後便在檢尺時百般刁難,號稱也是公事公辦,結果挨了知青的幾下硬拳。這下事情可鬧大了,林場方面揚言要核實我們生產隊的運木頭路線,重新商量給我們的工錢。事關生產隊的收入和每個人的利益,一些原先支持阿安的知青也開始責備他太死板,缺少當幹部的靈活性。
阿安無可奈何地隨著許會計帶著禮物一齊向小羅賠禮道歉,還請林場的領導喝了酒。
在酒桌上,武主任語重心長地對阿安說,“小夥子,好好學著點,別那樣死心眼,學校教你們的那套玩藝在社會上根本行不通。這社會複雜得很,毛主席要你們上山下鄉,不就是要你們在社會這個大學校裏長長見識嗎?哈哈!”
(待續)
【文章照片選自網上來源:老知青家園】









